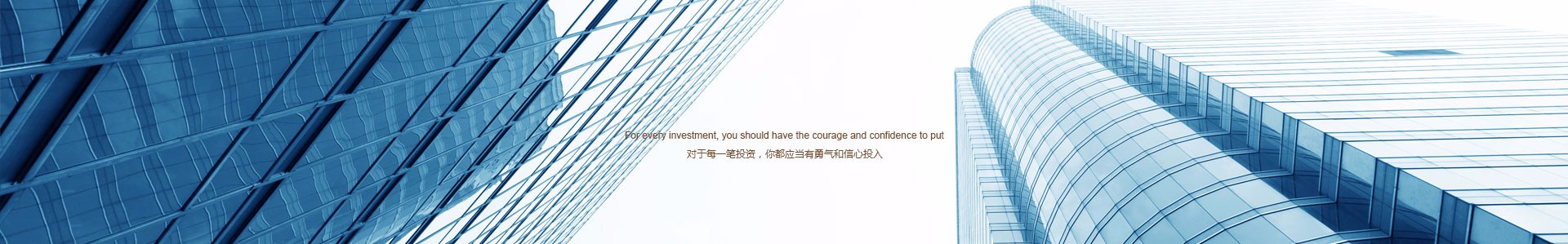徐太妃与徐太后:笔尖流淌的彭州诗意藏着千年风华
2025-11-08在五代十国的乱世烽烟中,前蜀的两位徐姓女子以笔墨为舟,在彭州的山水间留下了不灭的诗意。她们是徐耕的长女徐太妃与次女徐太后,两位曾权倾一时的女性,用八首传世诗作,为丹景山的云雾、阳平治的松风,注入了穿越千年的温柔与苍凉。

成都徐家的两位女儿,注定要与前蜀的命运紧密相连。唐末年间,她们一同被王建纳入后宫,开启了相似却又交织的人生轨迹。王建称帝后,长女封淑妃,次女封贵妃;待后主王衍即位,姐姐晋封翊圣太妃,妹妹册为顺圣太后。

这对姐妹不仅共享着皇室的尊荣,更共有一颗浸润诗心。史料记载,她们常一同游历山水,以诗唱和,尤其在咸康元年(925年)那次著名的青城山之行中,姐妹俩随王衍遍历丈人观、玄都观、丹景山等地,留下了多篇唱和之作。那些在山道间、古观内流淌的诗句,成了她们生命中最明媚的注脚。

谁能想到,这样的风雅时光竟如此短暂。同年十一月,前蜀灭亡,次年四月,她们随王衍赴洛阳途中,于秦川驿被杀。乱世中的诗意绽放,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无常。
丹景山,这座矗立在彭州大地的山峰,成了徐氏姐妹诗意挥洒的重要舞台。山上的金华宫与至德寺,在她们的笔下焕发出独特的光彩。

徐太妃在《和题金华宫》中,以“丹景山头宿梵宫,玉轮金辂驻虚空”开篇,将皇家仪仗与山间道观的空灵融为一体。“军持无水注寒碧,兰若有花开晚红”两句,更是以小见大,在器物与花草的细节中,透出山间的清寂与生机。而“我家帝子传王业,积善终期四海同”的收尾,又将个人情思与家国命运相连,显露出身处后宫却心怀天下的格局。

徐太后则在《题丹景山金华宫》中,描绘出另一番景致:“碧烟红雾扑人衣,宿露苍苔石径危”,开篇便以鲜明的色彩与触觉,勾勒出山间清晨的朦胧与清幽。“风巧解吹松上曲,蝶娇频采脸边脂”,以拟人化的笔触赋予风与蝶灵动的姿态,仿佛能看到蝴蝶在花丛中翩跹的身影,听到松风奏响的自然乐章。她在诗中更直言“好把身心清净处,角冠霞帔事希夷”,流露出对道家清静无为境界的向往。

丹景山南的至德寺(今三昧禅林),也进入了徐太后的诗境。“周回云水游丹景,因与真妃眺上方”,点出游览的背景与同行之人;“晴日晓升金晃曜,寒泉夜落玉丁当”,以“金晃曜”“玉丁当”等词语,绘出晴日晨光的璀璨与夜间泉落的清脆,声色并茂;“松梢月转禽栖影,柏径风牵麝食香”,在月光、禽影、松风、麝香中,营造出静谧而富有生趣的禅林夜景。最后“虔煠六铢宜祷祝,惟祈圣祚保遐昌”,则将个人的虔诚祈祷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相结合,尽显忧国之心。
阳平治,作为张道陵初设二十四治之首,其浓厚的道教氛围,也激发了徐氏姐妹的创作灵感。

徐太妃的《和题阳平》,开篇便充满仙气:“云浮翠辇届阳平,直似骖鸾到上清”,将皇家车驾抵达阳平的场景,比作乘坐鸾鸟飞升仙境,瞬间拉近了人间与天界的距离。“风起半崖闻虎啸,雨来当面见龙行”,以夸张的笔法写出山间风雨的气势,虎啸龙吟间,尽显阳平治的神秘与威严。“晚寻水涧听松韵,夜上星坛看月明”,则转向闲适的游览生活,听松韵、观月明,在自然中寻找心灵的宁静。而“长恐前身居此境,玉皇教向锦城生”一句,更是耐人寻味,流露出对阳平治这一仙境的眷恋,仿佛前世曾在此栖息,今生却被命运安排到繁华的都城。

徐太后的《题彭州阳平》,则更显平实与深沉。“寻真游胜境,巡礼到阳平”,直白点出游览的目的与地点;“水远波澜碧,山高气象清”,以简洁的语言勾勒出阳平山清水秀的整体风貌;“殿严孙氏貌,碑暗系师名”,将目光投向道观内的殿宇与石碑,在历史的痕迹中感受阳平治的厚重;“夜月登坛醮,松风森磬声”,描绘出夜间登坛祭祀的场景,松风与磬声交织,尽显道教仪式的庄严与神圣。
咸康元年的那次游历,成了徐氏姐妹人生中最后的诗意绽放。随着前蜀的灭亡,她们的生命戛然而止,但那些留在彭州山水间的诗句,却如丹景山的青松、阳平治的清泉,历经千年而不衰。

如今,当我们漫步在丹景山的石径上,仿佛仍能看到 “宿露苍苔” 的痕迹,听到“松上曲”与“虎啸龙吟”;当我们驻足阳平治的古观前,似乎还能感受到“云浮翠辇”的仙气,听到“松风森磬声”的悠远。
徐太妃与徐太后,这两位在乱世中绽放又凋零的女性,用她们的笔触,为彭州的山水注入了永恒的诗意。她们的故事,藏在丹景山的云雾里,躲在阳平治的松风中,成为千年彭州最动人的风华注脚。而那些流传至今的诗句,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命运,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纽带,让每一个来到彭州的人,都能在山水间,与千年前的诗意撞个满怀。